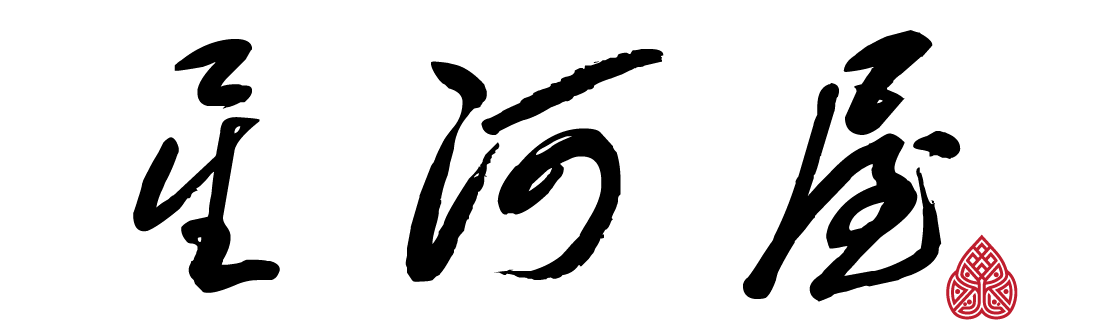DNA不会说谎 -1
- DNA不会说谎
- 2025-11-22 06:28:29
1
电话在桌上响起时,我正忙着为另一宗案件修改结论。
电话那头是律师协会里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声音前所未有地沉重:
“李律师,有个案子……我知道你忙,但想来想去,大概只有你敢接,也有能力处理。”
他停顿了一下,像在斟酌每一个字:
“是王亮的案子。 一审已经判了——强奸继女,十年。”
我的心一沉。王亮案曾经让全城舆论沸腾,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禽兽继父”的标题,公众群情激愤。对任何一个理智的律师来说,那都是烫手山芋,避之不及。
“一审法院已经判得很清楚了,证据也钉子一样牢。”
我试着委婉拒绝。
“他不服,坚决上诉。前一个律师也没办法。现在家都卖了,妻子几乎崩溃,他们凑了点钱,想孤注一掷最后一次。最关键的是……”
朋友压低声音,
“王亮在看守所绝食多日了,他只重复一句话:‘用我的命证明我的清白,可以吗?’”
那句话像一根冰冷的钉子,直直钉进我的心脏。
一个人绝望到愿意用性命来证明清白——要么是恶人演戏演到极致,要么是真正背负着滔天冤屈。
“一审的形势对他极度不利。”
老朋友补充,声音满是无力。
“那个女孩的证词没有一丝破绽,情绪真挚到能让人共鸣,陪审团当场还有人落泪。生物证据吻合度高得像钉死一样。最关键的是,案发时间他声称自己在家睡觉,但没人能替他作证。形势几乎是单方面的,绝望。”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在等我的回答。
而我面前的,不再只是一摞卷宗,而是一道选择。
接受这个案子,意味着我要赌上自己二十年来积累的全部声誉。
媒体会称我为“怪物的同路人”;同行会在背后窃窃私语,觉得我为了律师费而出卖良心。
如果输了,我失去的绝不只是一桩案件,我会成为整个司法体系的笑柄——那个狂妄到试图撬动一桩“铁案”的傻子。
这不仅是一场辩护,而是一场战争。
我必须面对的,不只是对我极其不利的证据、泪流满面的受害者形象,还要面对一审判决的权威、汹涌的舆论浪潮,以及司法体系对“已定罪者”那股巨大的惯性。
我将独自面对这一切,为一个被社会彻底抛弃的人说话。
理智在嘶喊,要我马上拒绝。
但那句话——那个绝望到愿意用性命控诉命运的声音——刺穿了所有嘈杂的算计。
它像一把钻子,钻穿了我作为律师的骄傲外壳,钻入最深的旧处:
那里藏着我初入行时的信念——相信“正义”值得我用全部心力追寻。
我讨厌这种感觉——幼稚、不够专业。
但我知道,如果今天挂断电话,往后的岁月里,我会无数次在夜里惊醒,只因为耳边回荡着那句:
“用我的命证明我的清白,可以吗?”
沉默持续了很久。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开口——平静,却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坚定:
“把一审的全部卷宗发给我。”
没等对方回应,我又补了一句——既是对他说,也像是在宣判自己未来的命运:
“告诉他,我接下上诉案。但也让他做好准备:这条路,要么通往无罪,要么我们一起坠入深渊。准备好再走。”
我挂断电话。办公室静得像坟墓。我深吸一口气,打开邮箱,等待那封可能改变我人生的邮件。
不久后,提示音响起。标题写着:
“王亮强奸案一审卷宗”。
我再次深吸一口成人小说平台气,点开邮件。
冰冷的文字与成堆的照片仿佛把我一把推向无底深渊,令人窒息。
映入眼帘的第一份材料,是受害者的笔录。
每一行字都整齐得令人发毛,细节完整得近乎可怕——时间、地点,甚至王亮 allegedly 说过的侮辱性话语,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
我试着找漏洞,但多次询问笔录显示:核心内容始终如一,稳定到像被钢板焊死。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怎么能把那种肮脏的细节复述得如此完美,而不露出一丝破绽?
这些口供,看起来更像是经过反复排练的剧本。
我心底暗暗希望生物证据能出现哪怕一丝疏漏。
但DNA鉴定报告几乎就是一份死亡判决。
结果写着 STR 基因型完全吻合,而“概率比”显示的错误可能小于十亿分之一。
十亿分之一——在法庭上,这意味着绝对确定。
这是一份冰冷、不容撼动的科学证据。
我的指尖渐渐冷了下来。
我快速翻到证人笔录,希望找到一点点松动。
受害者母亲张薇的陈述满是痛苦与自责:
“我没保护好女儿。”——“我恨他。”
一个破碎母亲的形象,足以撼动任何人的心。
而闺蜜的证词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她确认在报警后,李小娜曾泣不成声地打电话给她,而那些哭诉的内容与警方笔录完全一致。
动机与不在场证明也同样无处可躲。
双方都承认:王亮与李小娜之间长期存在矛盾,原因是“管教严格”。
卷宗里还写着一个“道德死穴”:
婚初王亮曾向张薇谎报经济状况。
检察官在一审时狠狠击中了这一点:
“一个连妻子都能欺骗的人,他在法庭上的誓言还有多少可信度?”
至于案发时间,王亮拿不出任何不在场证据。他的唯一说法只是:
“我在家睡觉。”
我合上卷宗,向椅背倒去,一阵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向胸口逼来。
所有证据精准咬合,逻辑紧密得像铜墙铁壁,把王亮死死压在最底层。
理智早已为他宣读了死刑。
但职业本能——像心电图上微弱但顽强的心跳——仍没有完全消失。
正是这种本能,让我下意识记住了几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
过于完美的口供、精确得令人发寒的DNA采集位置……
我知道,也许这一切都是徒劳。
但我的脑子已经开始自行运转,哪怕意志力叫我停下。
我已经没有退路。
我的战争正式开始。
而第一战,就是会见那名深陷绝望,却仍坚称自己无罪的男人。
2
看守所会见室,隔着一块冰冷的玻璃。
王亮坐在对面,比照片上还要憔悴,眼神几乎完全黯淡,只剩下一片浑浊的死寂。
“李律师……”
他的声音沙哑,如同砂纸摩擦般刺耳。
“谢谢你愿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