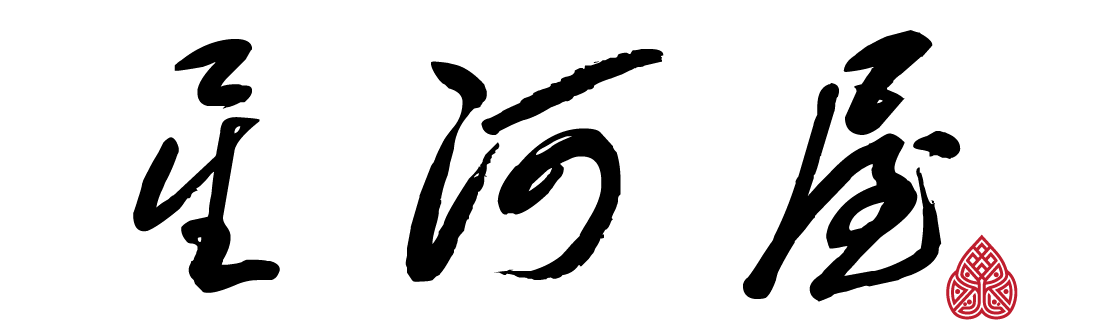DNA不会说谎 -3
- DNA不会说谎
- 2025-11-25 02:44:31
5
我拨通了号码,铃声响了七八声才有人接起。
“喂?”——一个女人的声音,疲惫却带着警惕。
“你好,李静女士,我是李哲,是王亮案件的辩护律师。我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
“我没什么可说的!”
她立刻打断,声音急促:
“我和我妈、和那个家里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们别再来找我!”
“但是在卷宗里写着,你妹妹曾经指控王亮也曾经……对你……”
“神经病!”
电话那头的声音突然变得尖刻、苦涩:
“王亮那种人,只会支支吾吾,根本做不出什么事,他敢碰我?他试试看!我妹妹现在都疯了,见谁咬谁!你们非得把我也拖下水吗?我工作刚有点起色,我婆家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求求你们,把我当成死了的人行不行?”
电话被猛地挂断。我把发烫的手机放回桌上,在名单里“李静”的名字旁画了一个叉。
我对她的反应并不意外——甚至能准确猜到她在一审时经历了什么。
那些已经和家里断绝关系,又有明显个人利益的证人,永远是公诉方最容易攻击的对象。他们会把她描绘成一个自私、冷漠、为了自保不惜说谎的人。
她的证词不仅无法动摇那一串“完美的证据链”,反而还可能被公诉利用来证明:“王亮被所有人抛弃,是品行低劣之人。”
老周在一审时把她叫出来作证,多半是一步错误的棋。
这条调查线索,也算是断了。
6
这一次,见面是在小区的花园里进行的。
张阿姨缩在长椅上,整个人瘦得像一片枯叶。
“张姐,我们需要再谈一谈。王亮当时——”
“没什么好说的成人小说平台了……”
她的眼神空洞。
“媒人介绍,说是老实人、能过日子……我累了,只想找个能依靠的……”
“结婚之后,他对你们母女怎么样?”
“也就那样吧……挣钱不多,不爱说话,跟孩子们合不来。”
她一直反复揉着衣角,动作机械而重复。
“案发那天,你——”
“啊——!”
一声短促的尖叫突然迸出。她抱住头,整个人抖得厉害。
“别问了!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记得!我女儿……我开门的时候,她就跪在那里……浑身发抖……她说,她说……”
她猛地抬起头,满脸泪水,痛苦、恐惧与近乎偏执的决绝混在一起,如同从深渊里撕裂出来:
“我还能怎么办?!我只想保护我的女儿!”
话音落下,她像被抽空了力量般瘫软下来,哭得断断续续,整个人快从椅子上滑落。
一个路人投来警惕的眼神。
我已经无法再问下去。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但她没有接。
我站起身离开,身后,是一位母亲再也压抑不住的绝望哭嚎。
7
女孩蜷缩在沙发上,头低得很低,十指紧紧交握。
她的父母分别坐在两侧,严肃得像两尊守门的石像。
“小时候小雅只抱怨过继父管得太严,不让穿短裙,也不准晚上出去玩……”
“她有没有说过任何越界的肢体行为?哪怕是很久以前的?”——我问。
女孩猛地一颤,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连连摇头:
“没有!从来没有!她只说觉得烦、觉得害怕。”
“案发当晚,她打电话给你,她说了什么?”
“她一直哭,哭得喘不过气,说‘他欺负我’,啊……‘爸爸欺负我’。后来好像她妈妈回来了,电话就被挂断了。那时候我吓傻了……”
母亲立刻抱住女儿的肩膀,用警惕的眼神看着我:
“警察……哦不,律师,孩子只知道这些。她也需要休息。”
我点点头,合上笔记本。
又一份几乎无懈可击的证词。
孩子眼里的恐惧是真实的,可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严丝合缝,完美填补了整个指控链条。
从李小雅到张薇,到现在的刘云——情绪都浓烈,却又彼此如同接连上演的同一场戏。
一个被打磨过、被反复排练过的剧本,只为了把王亮推向深渊。
让我绝望的不是这些证词本身,而是一个赤裸裸的事实:
我正被卷入一场已经重演无数次的戏剧,却找不到任何一处裂缝可以撕开那层华丽的幕布。
我站起身,道别离去。
8
电话刚接通,对面就传来一个男人吵吵嚷嚷、充满不耐的声音:
“李律师吗?什么事?我很忙。”
“我想问一下关于您的前妻——张薇,还有您的女儿,李小雅……”
“够了!”——他立刻打断,声音僵硬而冷。
“抚养费我每个月都按时打,一分不少。法院怎么判我就怎么做。除此之外,其他事与我无关。”
“那关于王亮……”
“我不认识!那是张薇自己找的男人,好坏都由她自己承担。我现在已经有新的家庭了,别把那边的破事再拖到我这里来。说到这就够了。”
随后,只剩下干巴巴的嘟嘟声。
简短。
决绝。
9
去问王亮的邻居比我想象的还要辛苦。
楼上新搬来的人满不在乎地说,不知道楼下发生了什么。对门的住户只稍微开了点门,敷衍地说了几句“关系不熟”、“没怎么注意”,就急忙关上了门。
最后,只有一位同层的银发大妈和住在王亮楼下的一对年轻夫妻愿意稍微分享一些情况。
大妈压低声音,像怕被别人听见:
“王亮啊……确实让张薇吃了不少苦。他话不多,但我觉得他算是关心家庭的人。下班回家就是直接回家。不过……有件事有点奇怪。
他很喜欢站在阳台上,尤其是晚上,大概十点、十一点,经常看到他独自站在黑暗里,不开灯。只有烟火闪烁的光,忽明忽暗,站上半个小时、一小时都有。”
楼下的年轻夫妻则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丈夫眼圈发黑,抱怨道:
“其他事情我不清楚,但有一件事我真受不了。他们家好像完全不隔音。几乎每晚都是这样,通常十点、十一点以后,就能听到洗衣机嗡嗡作响。有时候响一会儿,有时候甚至两小时。第二天早上我还得早起上班,累得要命。我曾敲门提醒过,他只点点头说‘对不起’,然后还是老样子。
说实话,越想越觉得怪,哪家半夜都要洗衣服啊?”
10
冰冷的会见玻璃把两个世界隔成两半。
王亮拿起话筒,手指微微发抖。
“李律师……谢谢你还愿意来……”
“王亮,我需要你尽量回忆清楚——”
“别问了。”
他打断我,声音空空荡荡,像一口干涸的井:
“没有用的!所有人都说我有罪,从警察、法官、记者……到我老婆……她一次都没来看过我。也许我真的有罪。我认了。我不想再上诉了……太累了……”
他放下话筒,没有再看我一眼,弯着背,跟着狱警缓慢离开。
那个背影,就像一个刚刚失去整个世界的人。
走出看守所,午后的阳光刺眼得令人发痛,但我心里却没有一丝温度。
一种前所未有的空洞感正把我一点一点勒紧。
我的当事人——那个本该是这场战斗中第一束火焰的人——亲手把火熄灭了。
“我一直相信‘公平至上’——但此刻,在这种绝望到极点的面前,那句信条显得苍白、可笑,甚至有些虚伪。
我到底是在为谁而战?
为一个甚至连自己都不想活下去的当事人?
还是为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真相?
我用了二十年职业生涯筑起的信念之墙,在王亮那死寂的眼神下,悄悄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我开始动摇。
而就在我最脆弱的那一瞬间,来自我整个世界的声响——像早已瞄准的子弹——铺天盖地朝我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