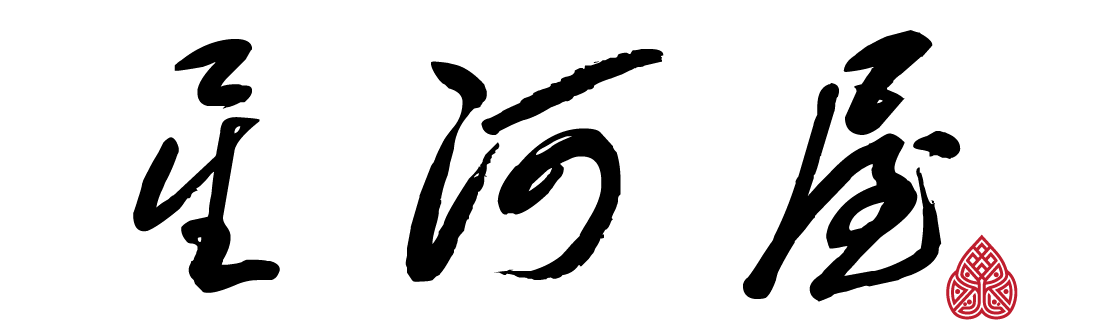DNA不会说谎 -2
- DNA不会说谎
- 2025-11-24 02:36:15
“王亮。”我打断了他的客套话。
“我不需要你感谢。我也不想听你喊冤。
我只要你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无论它多愚蠢、多重复,甚至会让你觉得羞耻。明白了吗?”
他那双浑浊的眼睛望着我,然后慢慢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从八点到十二点,你到底在做什么?每个细节都说一遍。”
“我……我在家睡觉……”
“睡觉前呢?看了什么电视节目?有没有换频道?中间有没有插播广告?”
“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新闻……我也没怎么注意……”
“那手机呢?你有没有下意识拿起来看过时间?那时候电量还剩多少?”
“好像……好像瞥了一眼……电快没了,所以我就充电……”
“有没有什么声音把你吵醒?狗叫?汽车喇叭?楼下邻居吵架?”
“没有……我睡得很沉……”
他的回答模糊、空洞、毫无确定性。
每个问题像是落进棉花里,没有一点有力的反弹。
他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力气和方向,只是机械地重复:
“我睡着了。”
这种无力感让我气得几乎要爆炸。
我改变策略,直接抛出致命的道德污点。
“王亮,档案上写着你曾经对张薇隐瞒过自己的经济状况。是不是这样?”
他的脸一下子刷白,羞愧地低下头,声音几乎听不清:
“是。我……当时糊涂……怕她嫌弃……后来我很后悔……”
“你知道这件事让你在法庭上说出的‘我没有做’三个字变得多么空洞吗?”
我的语气忍不住变得严厉。
“我知道。”
他抬起头,眼中满是绝望。
“所以我才说成人小说平台……只剩这条命能证明了……”
会面结束。
看着他佝偻的背影被带走,我没有同情,只有令人窒息的沉重。
我的当事人连一条能为自己洗清嫌疑的证据都没有,反而背着不诚实的污点。
除了用命来表明清白,他别无选择。
而我,作为律师,必须找到连他自己都看不到的出路。
前方是深渊,而我也正一点点滑向那里。
3
走出看守所时,刺眼的烈日正高悬头顶,但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
王亮的绝望就像一件湿透的棉衣,紧紧贴在我身上,冰冷又沉重。
我提醒自己:不能掉进那种情绪深渊里。
我是律师,我的武器是逻辑和证据。
而这场战斗,我必须从拆解、击碎检方搭建的那座“完美堡垒”开始。
我列出了一长串需要去见的人。
第一个,当然是曾在一审中为王亮辩护的律师——老周。
但会面毫无收获。
老周没有带来一丝希望,反而给了我当头一盆冷水。
他回忆王亮在法庭上的状态:糟糕到了极点。
有几次他刚开口说出对自己有利的内容,马上就被检察官一刀封喉:
“一个曾经欺骗过别人的人的誓言,有什么可信度?”
老周也试过“报复”这个方向——暗示李小娜可能因为怨恨而编造指控。
但刚说到一半,就被检方利落反击:
“有哪个女孩会拿自己的清白来报复别人?”
仅这一句话,就让陪审团明显倒向了他们,所有反驳都被堵死。
最致命的是:检方的证据链严密得几乎无懈可击。
李小娜在证人席上的形象,简直像一堂关于“完美受害者”的示范课。
每一个表情、每一滴眼泪,都精准击中了陪审团的情绪,尤其是女性成员。
只有一个细节让老周觉得有点奇怪:
李小娜和她母亲的情绪反应似乎“同步得过于一致”,仿佛两人心跳是同一个节奏。
会面结束时,老周拍了拍我的肩膀,劝道:
“小姑娘,放手吧。
为一个罪名已经被钉死的人拼命,拿你二十年的名声去换,不值得。”
4
我向他道了声谢,然后起身离开。
那些话像一场冰冷的雨,狠狠泼下,把我心中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完全浇灭。
在他的眼里,前方只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
而我——必须是那个用头撞碎那堵墙的人。
如果从“辩护”这一侧找不到突破口,那么我的战场就只能转向“指控”的核心。
下一个目标,不必怀疑:
正是那个亲手把王亮推入深渊的人——李小娜。
我想亲自见见这个让老练如老周都束手无策、让陪审团落泪的女孩——那个“完美受害者”。
会面被安排在法院的心理咨询室内,营造出一个安全的氛围。
李小娜身边有她的母亲——张薇——以及一名社工。
她坐在我对面,双手紧紧抱着一个抱枕,脸色苍白。
她的眼神脆弱得像一只刚被惊吓的小鹿,但在那脆弱深处,却藏着某种难以捉摸的坚硬。
“小娜,我是王亮的律师,名字叫李哲。我知道这次会面可能让你不舒服。我不是来伤害你,而是想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情况。”
我故意放缓语速,声音轻柔。
她轻轻点头,却没有开口。
我选择从审判记录中一个不太敏感的细节切入。
“小娜,上次你说,当时你‘看到月光照得很亮’。
你能回忆得更清楚一点吗?月光是从哪个方向照进来的?照在他的左侧还是右侧?
这个细节对我重建现场、理解你的视角非常重要。”
我保持着一种像是在讨论技术问题的态度。
女孩明显怔住了,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眼泪立刻盈满眼眶,但声音却清晰得令人发冷:
“月光……月光照在他背上。他的影子把我整个盖住。”
“我看不到光,我只看到黑暗。”
我的心微微往下一沉。
这个回答不仅没有露出破绽,反而补充了新的细节,让她的叙述更加稳固。
只凭一句话,她就轻巧地把一个关于“月光方向”的技术问题,转化为一段充满情绪的控诉,强化了自己的受害者处境。
我心底掠过一抹寒意。
我不仅没找到漏洞,反而无意中帮她“丰富”了证词,使之更加动人、更加可靠。
在社工和她母亲的眼中,这几乎成了对“创伤记忆”的再一次确认。
我调整方向,触及核心动机。
“在事情发生之前,你和王亮……也就是你父亲的关系如何?”
我故意用“父亲”这个称呼来观察她的反应。
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我敏锐地捕捉到一瞬间极细小的紧绷。
“最大的矛盾是什么?”
“他看我不顺眼。”
回答脱口而出,像是被重复过无数次。
“我做什么他都管,穿什么、和谁玩、几点回家……他都要说。他觉得我让他丢脸。”
那是青少年常见的抱怨式控诉,情绪浓烈,却缺乏具体细节。
“小娜,在事情发生之前,全家一起吃饭或看电视时,气氛通常怎么样?
你母亲……她看起来幸福吗?”
我抛出一个重量级问题。
瞬间,我看到她的手指死死掐住抱枕。
旁边的张薇忍不住发出一声哽咽。
“我妈妈……”
泪水从李小娜的眼里倾泻而下。
“她太傻,被他骗得团团转。他根本不配我妈妈!”
又是一句情绪饱满的指责,却依旧内容空洞。
她再次巧妙地把问题引回对王亮的道德批判,避开对父母婚姻的具体评价。
四十五分钟的询问结束,我却一无所获。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完美受害者”:
沉溺在伤痛中,却冷静得近乎可怕;
情绪丰富,却丝毫不露破绽;
故事充满泪水,却没有任何可以撬动的缝隙。
当我离开时,社工看我的眼神已经毫不遮掩地写满了指责。
而当我意识到,自己的对手比想象中更强大、更老练时,绝望再一次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