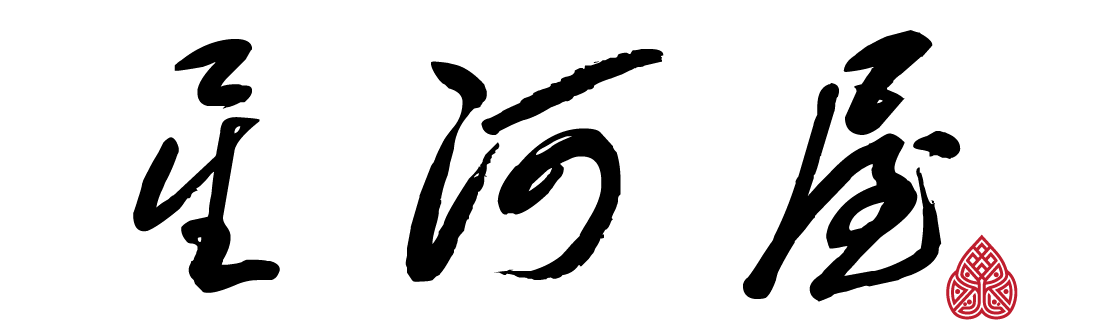那位我永远触及不到的你 -2
- 那位我永远触及不到的你
- 2025-11-19 02:39:32
白君坐在长榻上,手指轻轻掐着那双已添上些许花白的浓眉之间的空隙。台灯的光线因深色灯罩的遮挡,被收束在一个角落,正照向放在长榻旁小桌上的那幅照片——照片中的女人与绵素简直一模一样,更确切地说,是她年轻时的模样。
绵素冒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季暴雨奔跑而来,没有丝毫预兆,就像那场毫无警示便闯入她生命的仓促婚姻一般。某天,白君叫绵素进房,告诉她:她要结婚了。至于绵素会嫁给谁,那男人是什么样的人,性情、家世如何——这些绵素一概不能知道,也不能询问。
至少,她该知道那个即将被称为“丈夫”的人的名字吧——一个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久都要与她共度的人!至少,也该像最基本的相亲流程那样,给她一点了解的权利!至少,也该像白君在征询她意见般,告诉她将要把她嫁给什么样的家庭——一个她知道必定富贵而权势滔天的家族!至少,绵素明白,身为名门之后,她注定要承担那些随之而来的代价……!
然而,在二十四岁、过早成熟的心思里,绵素仍暗暗期待着,父亲能以最简单、最普通的方式尊重她,像父亲对待女儿那样。此刻,白君不是在询问意见,而是在下令——这是家中无意识形成的“命令—服从—执行”的传统。掌控经济者永远掌权。
绵素从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迫”——在严苛的环境中长大。“工、容、言、行”是她从幼年起就被教导的女子必备品德——幼到绵素根本不懂自己为何要学,也不懂为何必须做到。喝茶、读书这种看似雅致的兴趣,也必须日复一日练习,因为几天根本不足以养成“必须渗进血液里的习惯”。
长大后,绵素终于明白——一个“纯血贵族”家庭的女儿,必须从小被武装整齐,随时准备被推上名为“婚姻战场”的地方。那里表面上被冠以门当户对的“幸福”包装,实际上残酷得不亚于真正的杀戮战场。
绵素就这样在外壳沉静、冷淡中渐渐长大。她将所有所学融进生活,化为下意识的反射。当她下定决心要开启新的人生、建立新的身份时,她将那些伴随童年、伴随青春、伴随生命的习惯全部抛弃。生活竟如此荒诞!别人费尽心血学习高贵优雅,以求脱胎换骨、步入豪门、享受富丽人生;而绵素恰恰相反——她渴望拥有一个普通、朴素的生活,那种身边所有女孩都在拼命逃离、奔向富华世界的生活。
她匆匆锁门,甩下包,快步走向最里面的房间。小小的出租屋简陋朴素,墙面刷着深色漆——这大概是房东为了避免墙壁被弄脏而采取的“粗糙保护法”。怕上任租客退租时留下显眼污渍,只能无奈地全墙刷深色。却忘了,下任租客可能期待更明亮的空间。如今,绵素反而喜欢这种带着些许阴郁却温暖的深色调;它让她感觉自己真正地活着,孤独却安全,像被包裹在一个神秘世界里。看惯了外界千万种刺眼光芒,人反而会渴望一片简单的灰暗以换取平静。
她没有添置太多家具。进门直走到客厅,只有一张旧长榻对着前任租客留下的老电视——背后仍鼓着大大的显像管,与那些如今商店里展示的超薄、超高清液晶屏截然不同。它旧到有时会因接触不良而黑屏,或有画面却无声音。厨房与客厅相连,为节省空间——对这种单人出租屋而言其实并非必要,但能让租客感觉“被体贴”。
木质橱柜挂在嵌入式煤气炉上方,炉灶总是冰冷,从未被使用过——别说煮一桌丰盛的饭菜,连点燃取暖都没有。绵素会做饭,也喜欢做饭;但她明白,几乎没人愿意一人忙前忙后准备一桌能让三四个人吃饱的菜,然后独自落寞地吃完。因此,她渐渐失去动机。于是,她用随意的食物代替精致餐点——清晨一碗泡面代替以往由仆人端上的丰盛早餐,一杯无名茶代替曾经的名贵下午茶。聪明,是知道在环境中选择合适的替代,而不是继续侍奉旧习惯。
简单未必幸福,但幸福往往很简单。此刻,对绵素而言,安全就是幸福。她恐惧——恐惧再一次坐在那张过长餐桌前,看着对面永远冰冷空荡的位置;恐惧豪宅里虚伪的笑、尖刻的讽刺,以及 雪霞 的各种刻薄折磨——那个被父亲迎回来、取代母亲位置的女人;恐惧 黄峰 带着酒气奔向她、粗暴撕开她的睡衣——那件在第一晚之后便被他嫌弃为“无趣”“不够诱人”的衣物;恐惧回家时父亲那足以杀人的眼神,只因为她说:她不想继续这段婚姻。
绵素换上依旧朴素、不够“诱人”的睡衣,手拿白毛巾,慢慢擦拭湿透的长发。她轻轻倒在紧靠墙角的小床上,小床只够一人睡。泛黄的白床单像那些廉价钟点房里的布料。床外是一只两层床头柜,上面放着一盏小巧的床头灯,足够照亮,却不会刺眼。这个小家虽然简陋,却比那栋豪宅温暖得多。即便冰冷,那也是她出生、成长、拥有回忆的地方。母亲去世时她还很小,但那些拼凑的梦境里留下的思念从未消散。至少,每当想起母亲,绵素便得到一种安慰——无论去向何处,母亲始终在身边,从不让她孤单。
绵素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她只需要这样平静、轻柔的生活。然而,平静从未能维持太久。她无法真正逃脱上层阶级的巨大阴影。某些不知名的力量总在暗中追逐着她,仿佛只等时机摧毁她才刚刚萌芽的微小幸福。久而久之,一个念头在她心底悄然浮现:
——难道自己这一生,就只能这样漂泊不定、颠沛流离?永远找不到落脚处,也得不到哪怕一丝微小的幸福吗?
陈珂走出电梯,身着一套深色西装,干练而利落,手上提着一只驼色皮质公文包——颜色颇为特别,与一般商务人士或办公室职员常用的皮包截然不同。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杯咖啡,杯壁蒙着一层由冷热交汇而凝成的细密水珠,半透明的杯身印着一层楼下咖啡店的标志。
陈珂扫视了一圈,员工的工作作风依旧没有达到她所要求的标准。她永远是公司里来得最早的那个人,今天也不例外。她有些无奈地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心想:早点来,或者至少准时来,有这么难吗?
办公室不大,却布置得极为干净、简单。中央是一张 L 型的办公桌,较长的一侧放着电脑和日常用品,另一侧则放着文件盘,也是陈珂用来放那只显眼驼色公文包的地方。靠墙的左侧是一组四层文件架,各类文件按编号、月份、年份整齐分类,标签贴得笔直又均匀。右侧是书架,上面三层摆满了枯燥的专业书籍——法学——最后一层则被助理雅柔悄悄塞进几本言情小说,让书架不要看起来太无趣。
放下咖啡,陈珂抬手在桌面划过一道长线。桌面干净得连一粒灰都没有。满意之后,她坐下。
敲门声响起,还没等陈珂开口,外面的人就扭动门把,直接推进来。是永昭——陈珂的上司。也不难猜,在这家公司里,除了他,谁敢不经允许就进她办公室?
陈珂不算难相处,但足够冷静、干脆、威严,让所有人对她既敬且畏。在工作中,她对员工的要求高、严格而精准;在社交中,她始终保持足够的界限,让人不至于产生越距的错觉。这样的距离感,让人对她颇有顾忌,但对她而言,这正好。至于员工间的交流,有雅柔——那个聪明、通透又能干的助理——就足够了。
永昭拉开椅子坐下。想他来干什么,对陈珂来说毫不困难。她在这里工作已久,凭案件成果赢得上司充分信任。
紧随永昭进来的,是雅柔,手上端着一杯刚出炉、热气腾腾的咖啡。她上前放在永昭面前。陈珂轻轻点头,雅柔便退了出去,顺手带上门。
“上一个案子耗了太久。”
永昭皱眉,不难看出他的不悦。
“对方坚持不肯和解,而林氏那边又不想把事情闹大!我只能亲自飞过去处理。”
“我不想这种情况再发生。”
“我明白。”陈珂点头。
永昭站起身走出去。这场对话短得惊人——短到雅柔捧来的咖啡还未散尽热气;短到外面员工都没反应过来,只见老板突然出现又突然离开;短到唯有陈珂知道,他为何一定要过来亲自说,而不是打一通电话。
永昭很少出现在公司,大部分工作都是电话、邮件交代,办公室的事务则交给陈珂及几位律师。
陈珂轻轻一笑,摇着头,对自己那点“小小的坏心眼”感到好笑——但确实是事实:永昭是个中央集权、冷淡又强势的人。思绪被桌上昂贵手机的震动声打断。陈珂讨厌嘈杂,也无法忍受过大的声音,因此即便独处,她的手机永远处于静音。
手机轻轻震动,让她这位喜静的人微微皱眉。她接起,声音拔高。
“说成人小说平台。”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件很搞笑的事。陈珂浓黑的眉瞬间舒展开,她忍不住噗嗤一笑,露出那颗少有人能看见的虎牙——她冷峻外表下唯一带着神秘感的可爱标记。
她的声音也柔了下来,甚至带点甜意。
“想我就讲直白点,还装!行行行!给美女的份我当然记得!你的就免了!这样吧!”
“他反应怎样?”
黄峰悠然地切着刚好五分熟的牛排,刀口整齐、轻柔。他用叉子送一块仍带红的肉进嘴。
“不是太满意,但也只能接受。”
伯林说着,把咖啡杯放下。
事情本就如黄峰预料,因此听伯林报告时,他显得十分得意。黄峰正要继续开口,旁边一位顾客不慎撞到服务生,整杯水洒向他。
黄峰条件反射般站起来,用餐巾擦掉西装上的水渍,将外套脱下挂在椅背。他挥手示意没关系,让服务生离开。随后利落地卷起衬衫袖子,左臂顿时露出一道约十厘米长的疤痕。
他和伯林同时看向那道疤,然后相视而笑。
那是无法忘却的记忆。
多年以前的一次登山,黄峰失足坠落,幸而抓住一个突出的石壁。那时,他的手臂被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血肉翻开,惨烈至极。即便如今他有钱也不愿修复,因为那是他的警钟:生死之间,距离真的近得可怕。
只有真正曾看见死亡之影的人,才懂得侥幸活下来的那一刻,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恩赐。那道疤,提醒着他珍惜现在,也提醒他永远感激把他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那个人。
当时,黄峰真的以为自己完了。伤口一阵比一阵更痛,力量也一点点流失。他知道,若再撑不住,他的明天、青春、梦想、家人……全都结束。绝望之中,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呼救。
然后——伯林出现,救了他。
他们的友谊,也从那一刻开始。
黄峰的性格一向清楚:别人给他一分,他必还一分。
所以这份救命之恩,他铭记在心,也必定要报。
“咚,咚”——敲门声没有打断白君的专注,他仍然盯着桌上打开的档案。等了一会儿,房门同时被推开,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脸上带着福相,身着一袭黑色中式服装,稳重而庄严的气度,使得他的身份显得格外神秘而古朴——那种人,人们常说是古时君王身边的“心腹”,虽未被赋予明确职务,但总是受人尊敬、掌握要事。
显然,朱廷在主人身边久了,已经明白此刻的白君状态并不适合报喜,也不适合报忧——尽管他带来的消息,并非完全不好。消息本身带有随时间变化而灵活的性质。也许此刻是坏消息,但在合适的时机,它会变成好消息。朱廷走近白君,简短地汇报了一句:
“小姐安全无恙!”
白君微微点头——轻到如果对面的人移开视线哪怕半秒,也会错过。朱廷本想多说些什么,但看着白君的神态,他觉得不宜再多言。行礼后,朱廷转身离开,房门缓缓合上,将他多年忠诚侍奉的视线与白君隔开。此刻,他知道,这个信息正合适。对于白君而言,绵素的安全意味着他必须准备好面对公司可能的严重危机;但在朱廷心底,绵素的平安,无论何时,都是好消息。
朱廷离开房间,沿着走廊缓步而行。外侧是栏杆,木制扶手沿走廊延伸,再顺着阶梯缓缓下降,阶梯用石头铺就,错落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金属细杆蜿蜒盘旋,简单的古典卷曲设计精巧而富有美感,为这座大宅增添了本就高雅的气质——这里是白君父亲,这位上世纪的智者倾注心血的所在。
大宅内饰富有浓厚的东方古典风格。仅从摆设便可看出主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如果用风水研究者的眼光粗略观察,从挑选家具到应用风水算法,都是为了与自己、子嗣、孙辈的命理相合——只为家道平安。这意味着,主人绝非以财富、名声为目标。这在一个传承风水学的家族中极不寻常,不免让白君怀疑:父亲为何要做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显然,父亲完全可以安排得更便捷高效,为何偏偏只执着于一件事?财富、名声不是同样重要吗?如果没有这些,这家族真的能顺遂吗?
一个纯商业思维的人,如白君,或许无法理解父亲的深思——一个始终想着积淀安宁生活、助人济世的智者。对白君而言,一切必须以数字衡量,以利润衡量,所有事物都必须发挥其最大价值,无一例外,无一豁免——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子女。
朱廷走下最后一级台阶,脚触光亮的地板,正欲朝正门走去。他停下脚步,望向客厅,那里传来“咔嗒”一声杯盏相碰的细微声音。一道女声响起——声音高亢清晰,却带着不友善的意味。
“那个小丫头怎么样?”
雪霞仍专注于手中的书,绝不看向朱廷,问出这样的问题,而她清楚,只有朱廷才能给她答案——尽管不确定他是否会如她所愿回答。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夫人。”朱廷神色审视。
雪霞猛地合上书——熟悉的怒意如往常。朱廷不常出现,但似乎每次出现,都会给雪霞带来无谓的苦涩——几乎二十年来,她一直自问,为何要承受来自一个非管家、非家人,也非朋友的人——只是一个极特别的人,而这种特别,不是属于她,而是属于她的丈夫——的这种苦涩。即便如此,雪霞也只能确认一点:白君的要求,对朱廷来说就是命令——生死都必须完成。
对白君而言,无人能替代朱廷,无人敢想削去他的地位,无论是谁。因为有几次——极少几次——当雪霞刚成为绵素的继母,成为家中女主角时,她在丈夫耳边低语那些任何男人都可能“嗯”过去、享受欢愉的事情,白君的反应却让她震惊——猛地起身,怒目而视,单字道:“不。”——只是因为她的话触及了朱廷的名字。直到现在,雪霞也只知道,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无人能解,而她其实无需理解,她只希望朱廷像对待“女主人”的身份那样尊重她——就如全家人对她称呼“夫人”的态度。
“若无其他事,我告辞了,夫人。”
朱廷似乎并不在意雪霞的态度,略显婉转地后退一步,然后转向正门,那里两扇木门精雕细琢,花纹对称,将门分为上下两部分。朱廷步伐更快更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此,将雪霞与她的恼怒隔开。
“对不起,先生!”——那位经理连忙走出,跟着把水洒出的员工拉到一边。
黄峰皱眉,对话被打断有些不悦,正要开口,伯林抢先说道:
“没事,你们回去工作吧。”
经理和那名员工连声道谢,退回岗位。黄峰心里颇不舒服,对他而言,过失已被原谅,就不要再带人出来打扰,尤其是在处理工作的关键时刻。伯林置之不理,靠在椅背上,翻阅档案,专注无比。
“你整天记得还我人情吗?就当利息吧!”
黄峰吐出一口气,似乎已习惯朋友这句话。总是心怀感激、珍惜朋友,但黄峰从未理解,为何伯林会站出来保护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当然,这不仅一次,而是多次为这所谓的“利息”。黄峰也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恼火,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变得更加沉稳、温和,甚至心思更宽容。显然,伯林的影响力足够大,足以逐渐改变一个人。友情并非债务,而是缘分——一种奇妙美好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