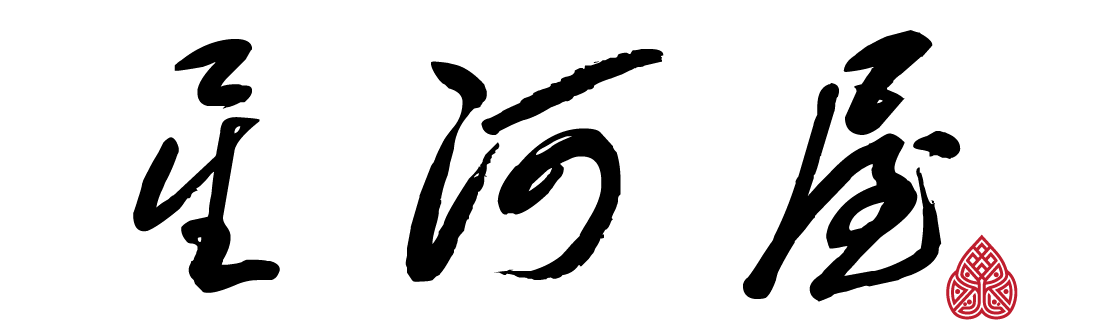那位我永远触及不到的你 -18
- 那位我永远触及不到的你
- 2025-12-04 04:56:04
灵堂的大厅足够宽敞,可容纳约一百人。一道白色帘幕将棺木与吊唁大厅隔开,把房间分成三部分:棺木占一部分,其余两部分是来宾吊唁的区域,左右两侧摆放着整齐的长椅,每侧五排、每排六张。巨幅遗像前,被多层白玫瑰花环包围着的,是一张铺着长桌布、遮住四条桌脚的桌子。桌上是一排排白色蜡烛,插在看上去相当昂贵的烛台上,从白骏的遗像向外呈弧形排到桌边。桌子正中央摆着一个巨大的香炉;三支粗大香在里面燃烧,香烟缭绕不绝。
雪霞含着泪水,神情悲戚地站在一群人之中,大概正在讲述丈夫的骤然离世。在那一圈又一圈纯白色的挽联花圈之间——这是这个家族传统的颜色搭配,而那些与家族关系密切、或更准确地说,那些必须讨好这个家族的人,早就心知肚明——人们小声议论着原本被认为庞大的资产究竟会落入谁的手中,是那位精明的继室,还是会跟着那位不知去向的掌上明珠?他们也窃窃私语着这场铺张的葬礼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如电视剧般的阴谋:是不是妻子与年轻男子有染,被丈夫撞见后,两人合谋将其除掉。流言蜚语从不知节制!所以,即便在葬礼上,各种猜疑也毫不避讳地被说出口。每当有新的吊唁客进入时,那些嘈杂的声音又会突然安静下来。
陈珂和伯霖身着黑色西装,像普通吊唁宾客一样出现。经历过上次见面后,伯霖对雪霞来说已不再陌生;但即便陌生,在这种场合,伯霖也必须尽力表现得与雪霞熟识——这样对陈珂非常有利。伯霖没有刻意靠近正与宾客交谈的雪霞,而是走到一个适当的位置,让她能够注意到他的出现。果然如预料,雪霞立刻结束自己的悲痛话语,与一位客人道别后走向伯霖。
“我以个人名义前来吊唁。节哀顺变。”伯霖轻声说道,微微低头,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另一只手按着腹前的黑色领带下缘。
“你一个人来的吗?”雪霞试探道。
“我女朋友。”伯霖轻轻把手放在陈珂的肩上。
陈珂走到伯霖身旁,略微勾起嘴角,那是她在社交场合不得不露出的礼貌笑容。此刻,这笑容对她而言不过是为了方便寻找绵紫。但即便如此,她仍然保持冷静,没有露出焦急或失态。她也想仔细观察这个与绵紫共同生活多年的女人。那脸上的颓色不像是情感上的悲痛——虽然按理说那也算是“情感”,毕竟遗像中的男人是她曾经愿意作为替代品嫁给的人。
那种苦涩的神情间,雪霞的双眼偶尔会闪过一丝笑意,而那双眼如今已布满明显的鱼尾纹。或许这就是陈珂察觉到的异常之处。陈珂虽话不多,但在一些特别的时刻,她还是会开口。
“您的眼睛会笑。”陈珂微微扬起左侧唇角。
“你朋友似乎不太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雪霞试图掩饰。
伯霖瞥了陈珂一眼。显然,陈珂是在故意挑衅。她完全明白此刻最需要做的,是从雪霞的视线范围内消失,让对方越快忽视她越好。根本无需猜测伯霖那个眼神的含义——现在不是表现自己的对抗欲望的时候。于是陈珂主动离开。
“我过去那边坐一会儿。”陈珂快步走向靠近出口的外侧长椅。
“她有点累。”伯霖替她解释。“本不该在这种时候提到工作,但……”
雪霞观察着伯霖的态度。也许这个年轻人有难以启齿的事。她知道,虽然伯霖与皇峰没有血缘关系,也不是皇家子孙,但他在皇廷中的地位不低,尤其是,他的话语很有分量——甚至能影响那些最傲慢的权势人物。在绵紫的婚礼上,尽管皇峰因侍者将红酒洒在他纯白的西装上而大发雷霆,但伯霖只要走到他身边,说了几句,皇峰的怒火便平息了大半,可见伯霖绝非普通人物。
上次见面后,雪霞更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伯霖在皇廷的重要合约中担任核心角色。当然,最终决策权仍在皇峰手中,但雪霞很清楚:无论伯霖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借此接近皇峰,她绝不会错过。利用一个人的价值就像利用一件商品——完全可以买卖交换,只是看能否出到合适的价钱!没有人没有价格,如果不能用钱买到,那就用更多的钱买!
“我没事,你说吧。”
“我们能换个私密一点的地方谈吗?”
悦君看了看手上那只昂贵的金双色腕表。她一向有准时的习惯,总是会比约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到。但显然,与她相约的人并不重视这次会面,故意迟到。这一点反映在悦君沉静的脸色上,以及她面前那杯已经凉透的咖啡上。那张小圆木桌的高度刚好与她交叠着、不甚舒适的双腿齐平。她已经没有心情像平常一样搅拌香浓的咖啡再慢慢品尝,而是不停地看时间。时钟已经指向十二点。也就是说,她已经等了对方两个多小时。
一个身着西装的男人出现了。依旧是皇峰,却不再像往常那样对悦君彬彬有礼、温和体贴。皇峰身穿白衬衫、束得笔挺,领带与合身的黑色西裤相配,勾勒出他匀称的身形与修长的双腿。皇峰在悦君对面坐下,身体往椅背一靠,双腿交叠,态度冷淡而漠然。
“我和你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吗?”皇峰双手交握,把交叠的指节放在桌面上。
“你这是什么态度?!”悦君不满地质问。
“没什么。”皇峰依旧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负责任!事情明明是你挑起的不是吗?!”悦君愈发恼火。
“那又怎样?”
“那…你也该负责到底吧?!”
“那依你说,‘到底’是什么意思?把绵紫带回来,然后让我继续做她的丈夫吗?”
“……”
“你没资格指责我!我也没有义务听从任何人的安排!”
“可是,从一开始——”
“没有可是!你想怎么留住你的爱人,那是你自己的事!别把我拖进你们荒唐的爱情里!”皇峰放下交叠的腿,准备起身。
“我没有拖谁进来!一切都是因为你!是你逼我伤害我爱的人!”悦君提高了音量,嗓音也变得沙哑。
“你问问你自己!如果你不愿意,我逼得了你吗?!”皇峰停下动作,重新坐好,冷笑出声。
“像你这种人,懂什么是爱情?凭什么指责我?!”
“我是那种不懂爱情的人,那你就懂吗?”皇峰缓缓把冰冷的视线刺向悦君。
悦君僵住了。皇峰刚才说的是什么?!他凭什么把她和他归为同一类人?!他凭什么觉得她不懂爱?!不,她爱着陈珈,那是货真价实的爱情,谁都无权否定!他凭什么把自己那些恶劣的想法强加在悦君身上?!他又懂什么是爱,竟敢指责她?!他又曾经真正爱过谁?
悦君努力想夺回陈珈,又有什么错?陈珈本来就是属于悦君的。陈珈这个人,他的心,他的温柔,本来就是属于她的。她不想再像过去那些日子那样孤单、痛苦。她只是想再次回到陈珈怀里,像过去那样拥有安稳的夜、愉快的白天、简单的幸福。她的要求,并不奢侈、不贪心。
然而,就这样一点点愿望,她却得不到。
是绵紫!都是绵紫!是她夺走了悦君的一切,让悦君所有的付出都化为零。也是绵紫亲手终结了那段——悦君曾以为还有可能挽回的——与陈珈的爱情。
按理说,经历了这么多努力,这么多牺牲,悦君理应和陈珈获得幸福。任何争夺,都该有终点,有输有赢。或许现在陈珈因失去绵紫会痛苦一阵子,但未来的日子还长,他完全可以和悦君快乐、幸福。难道只有绵紫能给陈珈幸福吗?悦君也可以,就像她曾经做到的那样。把属于“曾经”的那些东西抢回来并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问题只是——值不值得。而对悦君来说,这是她这辈子最值得的事。
这些念头闪过,悦君微微颤抖——难道她真的明知绵紫离开会让陈珈痛苦,却还是故意把绵紫推开,让陈珈像当初因悦君离开那样再度受伤?难道,她的占有欲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她对陈珈的爱?她反问自己,这样的自私是否曾经出现过……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悦君的反应让皇峰更加笃定自己说的没错。皇峰谈不上有什么爱情经验,可以说,他几乎没爱过谁。但报刊电视里不是常把爱情歌颂得神圣得要命吗?说什么爱是牺牲,是愿意让对方幸福,哪怕自己痛苦。皇峰总觉得这些理论俗套、浪费时间、愚蠢至极。
直到他亲眼看见柏临疯狂、愚蠢地爱着陈珈,为了让陈珈幸福而默默牺牲了这么多年——那一刻,皇峰才懂,那些所谓的爱情金句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源于现实,由真实的人、真实的感情、真实的行动凝成一句句流传的词句。
皇峰掏出皮夹,抽出一张纸币——足够支付悦君那杯已经冷透的咖啡,以及刚端上桌还冒着些许热气的那杯——扔在桌上便起身离开。他懒得再看悦君挣扎在混乱思绪中的模样。
请谁喝一杯饮料,对皇峰来说毫不困难。但在此刻,他压根不想做。钱放下的那一瞬,他甚至觉得自己像把全部家当扔在桌上。但随即,他内在的绅士本能又迅速压过了对她的厌恶与轻蔑——毕竟,他是上层社会的人,该做的姿态不能差。金钱,对他而言不过是数字。
也许皇峰厌恶悦君,但他不能否认,在这段时间里,悦君确实有实力、有眼界、有个性;皇峰也曾迷恋过悦君,就像迷恋其他聪明的女人一样。只是,当他发现悦君不像那些围在他身边、渴求男人的女孩——当他发现悦君从未把爱情投向男人时——他失望、他厌恶,之前所有的赞赏也迅速被负面情绪掩盖。
陈珈踩在铺着繁复花纹地毯的长廊上,走得波澜不惊。长廊尽头,她拐入一条相对狭窄的小道——尽管狭窄,但依然宽到容得下三个人并排行走。偶尔,她的眼睛四处打量。房子实在太大,而人口却很少。
自踏入那扇高大、漆黑、带着威压感的铁门开始,陈珈便无法抗拒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尽管她知道自己不该被任何理由牵动。但巨大的庭院、修剪得精细无比的草地、那些看似珍稀昂贵、按特定规律摆放的植株……让她忍不住驻足。
她停在那些光滑石板铺出的草地小径前——对一个赶时间的人来说,这显然不是好选择。再走一段,近角落处,一棵古树巍峨伫立,枝桠自然伸展开来,正巧撑着一座白色秋千,旁边是人工湖。完美的风水设计!
陈珈忍不住驻足,赞叹这片庭院的主人。
白色别墅坐落在古树的斜对面,不高的台阶却足以营造出建筑的傲然姿态。半弧形栏杆托着成团的朱槿花,仿佛在提醒访客“懂得节制才是美”。陈珈小心踩上台阶,来到宽敞的平台,看着那些从地面延伸到几乎整层高度的巨大落地窗,又望向紧闭的大门。
寂静无声。
这时,本就应当如此。
陈珈与柏临被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的男子接应,引导他们右转,穿过一条布满紧闭门扉的长廊,进入尽头那间偌大的房间。
当陈珈面对那位身形与自己颇为相似的女佣时,略微愣了一下——都是高挑且略带硬朗的身段。但很快,她便注意到了女佣的制服:灰色直筒上衣、立领、袖口与下摆缀着黑色,纽扣是中式盘扣;下身是宽松的黑裤,方便行动。整体古典、利落,也非常契合这栋宅邸的风格。
“请问,您需要什么吗?”女佣礼貌询问。
“我想找洗手间。”陈珈快速回答。
“洗手间在——”女佣刚抬手指向方向,整个人便因被点中哑门穴而软倒。
陈珈急忙扶住她,抬起手指探向她鼻翼下。她相信自己的掌控力,但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她更不可能放任无辜者生死不顾。性格这种东西,一旦形成,就很难违背。
她推开右侧的房门,把昏迷的女佣放进去。不久后,她穿着那套制服重新出现。
这样,她就更有把握寻找绵紫,而不必担心引起过多注意。
陈珈沿着女佣走来的方向快步前进。有某种直觉告诉她,顺着那条路,她会找到绵紫。
走廊尽头,她看见两个黑衣、戴墨镜的男子笔直站在门口,纹丝不动。那里……是在看守绵紫吗?如果不是呢?她没有任何把握。
她停在远处观察,思考如何接近。如果硬闯?以她的身手,对付他们并不难。但这会惊动更多人,到时候,她还能顺利带绵紫离开吗?如果那里并不是他们关押绵紫的地方呢?
“怎么不去工作?站这里做什么?”一个年长的女声忽然响起,伴随用力按在她肩上的动作——陈珈吓了一跳,猛然转身。
“我……”陈珈结结巴巴,看着那位眯着眼端详自己的年长女子。
显然,对方没看清她的脸,只是凭习惯呵斥。那身衣着——从花纹到裙装——明显比普通女佣高一个层级,也许是总管之类的人物。
不等陈珈回应,那女人又说:
“我不是说了吗,夫人吩咐过,让你们离那个地方远一点!你怎么老是鬼鬼祟祟?想被开除是不是?”
“不是的……”陈珈压低声音,尽量模糊语调。
“快去干活!”
陈珈走开,拐入走廊另一侧,在墙壁的凹陷处停下。那墙上挂着一幅昂贵的山水画,下方是一盆玉露,稳稳摆在与旁边木桌同色的木质底座上。
“女主人吩咐要远离那里”?
这是否意味着绵姝极有可能就在里面?
可是一切都还不确定,说不定那只是个存放贵重物品的房间,或者是主人家不希望下人靠近的重要地方?有钱人,总会有些难以理解的想法和行为。陈柯也不想多探究。刚准备离开,她却在听到有人说话时猛然停住了脚步。
“小姐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不吃不喝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会不会……”
“嘘!别乱说!传到女主人耳朵里……你就知道后果了!”
“哦!哦!……算了,快走吧!让女主人看到我们在这附近走来走去就麻烦了!”
两个佣人从陈柯藏身的交叉走道旁经过。他们一定把绵姝关在里面!肯定是这样!陈柯该怎么办?!无论如何,她都必须把绵姝救出去,无论要用什么办法。
但此刻,听到两名佣人的对话后,陈柯心乱如麻。绵姝已经虚弱到极点,多日不吃不喝,她怎么可能撑得住?绵姝本就体弱,如今情况只会更糟。想到这里,陈柯心如刀绞……她明白,在这种紧要关头,她不能慌!越慌,只会让绵姝陷入更深的危险。陈柯必须冷静,只有冷静,才能找办法把绵姝带回身边,带回过去那些平静的日子。
思索间,陈柯瞥见微微开启的房门,注意到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盖得严严实实、带着蓝色花纹的瓷杯。
“去哪?!”—— 左边的男人伸手挡住了陈柯。
“女主人吩咐我送参茶来。”—— 陈柯举起瓷杯,语气镇定。
“我以前没见过你?”—— 另一名男人疑惑。
“我昨天才来,大家不是都忙着处理老爷的丧事吗?”—— 陈柯随口编造。
“拿来!”—— 男人伸手想抢杯子。
“女主人要我亲自喂小姐喝!”—— 陈柯迅速把杯子缩开,又马上递出去。
“算了,你喂也行,我省点力。”
两名男人互相对视,又看了看她。似乎有些迟疑,最后其中一人主动打开门让她进去。
双腿发软,陈柯差点跪下去。绵姝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脸消瘦苍白,嘴唇干裂发白。陈柯觉得心脏像被丢进火里焚烧,体温直线上升。
如果陈柯能更早察觉一切就好了。
如果在知道事情的那一刻,她坦率告诉绵姝自己所有的想法,不再默默爱着、默默保护着,不让绵姝离开就好了。
如果她能更早找到绵姝……
陈柯将瓷杯放在门口旁的桌上,快步走到床边。
绵姝呼吸沉重。她非常清楚自己的状况。她知道自己的身体无法承受多日不吃不喝。
所以她选择了这种方式。
事实上,即便不是这种方式,她也会选一种同样本质的方式——一种自我消耗、自我毁灭的方式。只是,这在目前,是最可行的方法。
绵姝并不是逆来顺受的人,不会任由命运这股狂浪冲击、吞没自己的生命。
不对——也不完全对。
这些年来,她确实一直被命运的巨浪吞噬着。她接受它,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再怎么忍耐,只是压抑;终有一天,她会崩开、反击、逃离命运——那个她从小被灌输必须接受的命运。
绵姝不想再继续活成一个被用来交换利益的物品——真正意义上的交换。
在这栋宅子里,无论什么时候,她都不敢忘记那些期待她带来价值的人。因为父母,因为家族的事业,因为这栋豪宅的存在,因为里里外外几十号仆人赖以为生的成人小说平台饭碗……绵姝承担了超出自身的责任。
但当她终于想抛下那些她不该背负的责任,想逃离、想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她也曾问过自己——
如果她幸福了,会不会让很多人因此痛苦?
绵姝选择陈柯。
选择陈柯带给她的巨大幸福。
这种“巨大”,不是物质的奢华,而是陈柯的心、陈柯的爱——胜过世间一切。
陈柯选择了一个无家世、无背景、什么都没有的她……
而如陈柯说的那样,
陈柯根本不是“选择”她,
只是——陈柯爱她,仅此而已。
陈柯从未问过她任何事情。
她对爱情的理解很奇怪——
陈柯说:“爱不像办案,不需要把所有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唯一必须弄清楚的,就是对方是否真心爱你。”
绵姝总被她这些怪论逗笑。
仿佛全世界只有陈柯能想出这些话。别人谈恋爱要考虑经济、家庭、外貌、欲望,然后才是感情。
而陈柯完全相反——只要爱就够了。
对陈柯来说,绵姝的心,绵姝的爱,才是最重要的。